男女主角分别是的美文同人小说《乾坤之行》,由网络作家“佚名”所著,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本站纯净无弹窗,精彩内容欢迎阅读!小说详情介绍:一个少年,一个尚未知道出路在哪里的普通读书人。无意获一神奇莫测乾坤石,彻底改变与世浮沉、草间存活的命运。从此,身涉修真界这个最大江湖,行走乾坤,难以停息。人生际遇,动止纷纭;宇宙万象,变化莫测。他是如何高飞远翔、无畏阔步于大道之路,上演了三千大千世界的修真传奇。...
《乾坤之行》精彩片段
天脉大陆大津国南部山区,万峰耸峙,千沟百壑,群山环抱之中,恰有一山间平原丘陵地带,东西长二百多里,南北宽一百多里,明新州的州城正座落于此一地带的中部。
大陆上的城镇大多择水而居,一是为了人们生活上的便利,二是其传统的风水学上所讲的“得水为上”一说,明新的州城亦不例外。
明新江,其水发源于东南五百余里处的飞龙山,绕城而过,向西百余里之后再转向北缓缓流去,曲折逶迤千有余里。
关于明新州其名称的来历,流传甚为久远,由官府编著的《明新州志》里面颇为有板有眼,郑重其事的这样写着:
“盖于古时,州境之内,万山之中,天柱之上,尝于日入天暗后,登巅西望,日影犹印空中,如新日再复出现,故名“明新”。后有人将山中天柱削坏,以致山移柱崩,江河倒转,日影不复如前。”
然而,对于这种说法,就是明新州的当地人也会嗤之以鼻,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它,毕竟,这太过于违背常理。
因为按州志上所说的,那可是太阳从西边升起,或者是时光倒流,令人不可思议。
但,无论人们相信与否,斗转星移,日月如梭,几万年以来,这个神奇的传说就如流淌不息的明新江水,悠然不止,一代又一代默默地传承了下来。
初秋黎明,天高露浓,西边天际依然悬挂着一轮皎洁的弯月,正向宁静的大地不断地挥洒着清冷的凉光。
第三道鸡鸣声尚未叫唤起来,州城南郊二十余里的文理村周围成片成片的竹林、果树、谷子地里,此唱彼应地演奏着秋虫的唧令交响乐曲。
乡间蜿蜒的野草丛丛的小路,一颗颗柳树在路边静静地垂着纤细柔长的枝条,随着秋风闻风舞动,婆娑的荫影,时隐时现,变动不居。
村子里面的绝大多数村民们,如同大陆上许许多多的普通人一样,经过白天秋收的劳作,此时,还在深沉的酣睡中。
当然,在这个平常的表面之下,有一个年轻人的情况就显得特殊一些了——
文理村的外围,西边半里之处,有一座约十丈许高的圆形山墩,状如满月,山顶十分平缓,约莫有十来亩宽,上面种了很多高大乔木和果树,东边有一两亩大的渔塘,三间东向的青砖瓦房子正建于此塘之后,被掩盖在郁郁葱葱的树枝中。
一少年起了床,摸索到大厅正堂前面的桌子旁边,找到了固定放置于桌上正中位置的“火镰”,取出火绒豆许,放在石上,再用旁边的铁刃猛然一撞,“咔嚓”,黑暗中顿时擦出点点火星,“呼!”,火绒瞬间燃烧起来,并被点上灯芯,“哗啦!”,刹时橙黄色的灯光透亮了整个屋子。
柳义今年已满十六岁,中等身材,相貌也甚为普通,只是体格极为健壮,双眉比常人要粗黑些,眉尾稍往上翘,双目精光内敛,透出坚毅之神色。
其实,他的祖上并非明新州的当地人,实为距此数千里之遥的龙化州人氏,先辈曾出过武进士,系当地一小望族。
祖父是当时有名的神医,同时也是身怀武艺,但在其年轻时竟然得罪了一权势滔天的世家官僚,在那里呆不下去了,就宣布从柳家的家族中分出,并与之撇开关系,形同井水不犯河水,随之才流落搬迁到这边。
其后,凭着高深的医术,风栉雨沐,早出晚归,勤俭持家,终于在晚年时,置下了些许产业,包括文理村的这个祖宅及周边几十亩山地。
父亲柳敬倒也能继承祖上的医术和武艺,十五岁时就随其父行医,始终坚持“治病救人”和“医者父母心”的祖训,劳劳碌碌,饱经风霜,三十岁那一年,他用积攒多年的银两,在州城东门街一当行处盘下一个铺面以及后排的几间房子,开了一家名叫“仁和堂”的医馆,并把全家人都搬到了那里定居了下来。
至此,终日四处奔波的游方郎中生活才有所改变,取而代之的是坐在医馆里面帮人诊治,兼收购贩卖些药材,由于为人诚实守信,医术精湛,价钱公道,童叟无欺,平时甚至也常周济一些穷苦人家,从医三十五年以来救死扶伤,助人无数。
母王氏,随父打理医馆。
柳义有一兄一弟,其兄柳仁年已二十,为人纳言敏行,精明强干,自幼不甚喜诗书,迷心于研究岐黄,坚持不懈,以继承祖上的医术和武艺为已任,常怀救人之心,为柳敬当前之医馆中的最大助力。
其弟柳智,年方十岁,聪明伶俐,性甚机敏,正在老家文理村跟随一个叫“孟夫子”的文武全才的长辈,并在他的私塾中读蒙学。
和父亲及大哥不同,柳义对于祖上之医术,只是浅偿辄止,掌握些基本的知识和技艺而已。
但不知何故,他竟然自小便对天脉人传统的文武之道相当感地兴趣,在习练家传及各种武学之时极为上心,甚至达到了痴迷的地步;同时,为人好学不倦,博览群书,不但精研了四书五经等经典,还广泛地涉猎到道、墨、兵、杂等多家书籍及领域。
自七岁经父亲“易子而教”,拜“孟夫子”为师进入蒙学以后,十四岁时竟然通过乡试中了秀才,得了功名,并获得朝庭每月拨付一两银子的固定俸禄,惹得整个东门街的街坊们羡慕不已,人人都说柳家祖上积了阴德。
父亲柳敬对此则不以为然,认为柳义博闻强记,性格坚韧,文章也写得不错,今后通过科举中个举人、甚至是中个进士什么的,金榜题名应该没有问题,确实也是一件光耀门庭、出人头地之事。
然而,当今大津国之官场已远非如同往日清明,大多为世家豪门所把持,异常的黑暗和龌龊,没有靠山没有势力之人,在官场里面十分难混,搞不好就是一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极有见地的柳义也是深以为然,接下来就再懒得去考什么举人、进士了。
毕竟以他的为人和个性,一般官场里面的卑躬屈膝和谄谀取容已是让他望而却步,如果还要非对那些世家豪门奴颜婢膝、吮痈舐痔才能够获取富贵,那么,就是把他打死,也不会去做那些事情的。
对于未来人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他目前认为自己还比较年轻,今后或许是经商?还是教书?亦或是又回过头去跟父亲学医?……都没有定下什么具体的目标。
虽是如此,由于柳义写得一手的好文章,又得了功名,他还是成为了很多人的榜样。
街坊们时不时携带自家小孩登门拜访讨教,即便他有着一副好脾气,性格也爽朗,由于喜好清静,又有些与年龄不甚相称的成熟与稳重,所以在同龄人中也没几个朋友。同时,他也嫌医馆人多事杂,遂借口跑到文理村,名之曰照看祖宅,实则是图个闲散,以专心修文炼武。
“读书只为明理,练武方能强身”
此为柳义自己经过思考多年总结出来的道理,也是他奉为圭旨的人生信条。
也就是说:即使今后无意于官场,但是人生在世,明白事理和强身健体那可是必须的,所以,读书和练武这两件事他还是不改初衷,风雨无阻,持之以恒。
甚至,对于武道,在其心目中,时常有一种追求极至地强烈冲动和憧憬。
借着豆大的灯光,约莫花了半个时辰的时间研究一下几本书,包括《道德经讲义》和几十天前从“孟夫子”处借来的那一本叫《望气真解》的。
“吱呀”的一声拉开两扇木门,冒着当面送来阵阵凉风,柳义不禁深吸了一口气,徐徐吐出身体内脏中的浊气,迈开步子走到院子中间,活动了一下身子。
随之向东而站,双脚平行撑开,到距离三个脚掌之长度时,缓缓蹲下,两手环抱于胸前,如抱球状,双目垂帘微闭,同时默念:含胸拔背,虚灵顶劲的口诀,开始了每天必修的功课——扎马步桩。
不到两盏茶的功夫,柳义的呼吸节奏逐步地平静起来,气息渐渐沉静而凝实。接着,他的身子仿佛随着气息的流动微微上下浮动起来,远远望去,极似一个人正骑着马在宽阔平坦的原野上轻快前行。
不久,在淡淡的月光下,他的身上竟然隐约产生出一丝丝“雾气”,匝绕周身,越来越浓。
马步不知是创于何时,然而它确是天脉人几万年以来习练武术最基本的功夫之一,所谓“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因此各门各派绝大部分均有“入门先站三年桩”、“要学打先扎马”的说法。
柳义所练的马步桩,双脚分开略宽于肩,采半蹲姿态,因姿势有如骑马一般,而且如桩柱般稳固,因而得名。
通过练习马步主要是为了调节“精、气、神”,完成对气血的调节、精神的修养的训练,锻炼对意念和意识的控制。
在蹲马步的时候,各派均要求凝神静气,呼吸自然,蹲得深、平、稳,直接练习喉、胸、肾等器官,并使腹部肌肉缩进,腿步肌肉紧张,以图达到全身性的综合训练。
这种桩功,由于是长时间的静功,所以对于人体全身各器官是很好的锻炼,通过这样的锻炼能够有效的提升在剧烈运动时人体的反应能力,并可壮肾腰,强筋补气,调节精气神,且下盘稳固,平衡能力好,还能提升身体的反应能力。
修炼马步桩,随着功夫逐步深入,一般来说可以达到以下几方面效果:
一、每天习练,坚持三年之后,整个人会神奇地变为力大千斤,而且平时行走如飞、饭量大增;
二、体内真气猛增,充沛通畅,小腹时有热团;
三、精力异常充沛,口中津液常满,每天睡觉的时间可大大少于常人;
四、如功夫下得深,则内气鼓荡,可随意而行,运之于体内及体表;
五、功夫进一步,可达“心手相应、得心应手”之境;
六、如人有小疾,可应手而解。如打坐修道,可迅速入静,即所谓助道品也;
七、功深到极处,甚至可达“仙人指路”之效,也就是出现一些预测之类的神通。
自十岁开始随父练武,他的马步桩功足蹲了六年之多,且天天如此、寒暑不辍,上述前六个境界已全部达到,只是第七个境界要涉及到据说是涉及到了一些修真的入门秘法,单纯靠练武,非夙缘慧力深厚者很难悟到,所以一直未能突破。
整整半个时辰过去,蓦地,周身的雾气似乎开始有些淆乱,慢慢地发生不规则地扭曲变动,好象是被风吹散开的样子。
猛然从静定中回过神,心头一紧,柳义便知道今天的马步桩功火候已到,再勉强下去非只无益,反而有害。
随即意守丹田片刻,用力呼了几口气,“收功!”,缓缓起身,此时,这个少年全身上下已是被汗水湿透。
“哗啦!”,将上身短褂脱下,稍息片刻,接着又在地上打起了家传的“五形拳”——龙、蛇、虎、豹、鹤形拳。
“五形拳”据说为柳义祖上于天脉大陆上一宗门所习得,其法脱胎于天脉人博大精深的五行学说,揉和了龙、蛇、虎、豹、鹤五种动物的运动和搏击精华。
所谓:“龙应木,蛇应水,虎应金,豹应土,鹤应火”,鹤拳练精,蛇拳练气,龙拳练神,虎拳练骨,豹拳练力。
其拳理相生相克,刚柔相济,应物无穷,内外兼修。招式上攻守兼顾,劲道凌励,变化多端,暗藏杀机。
在天脉大陆上可以排到九级的武学秘籍,算得上是比较靠前的了。
武术、医术在天脉大陆上的流传由来已久,据说是圣人们在阴阳五行这些天道法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让人们修习,强身健体,进而体悟天道。
同时,天脉大陆面积广袤无比,东西南北不知纵横几亿万里,人类聚居生产活动的地方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更有无数未知的疆域,如:
深山大泽,万里荒漠,千里冰原,海外荒岛等等常人远未涉足,而那里是飞禽走兽、豺狼虎豹的天下,甚至还有令人闻之色变的妖禽怪兽,就是在一些偏僻的小型聚居区,人类还时常受到袭扰。
因而,一直以来,除了那些一心读书求取功名而没有时间或者没有精力去练武的读书人,天脉大陆上的一般人为了强身健体、保家卫园,大都以武为本,尚武成风。
天脉大陆武学亦有九个层次,一级为最低,俗称“入流”,九级为最高,一级到九级均属后天范围,一律称为武师,突破了九级的称之为“先天”,成为先天的武师便可沟通天地中先天之真气,并可外发于体外,杀人于无形,且威力强大。同时,先天之后,他们的寿命就是凡人的一倍,达二百多岁。
所以,达到先天的层次是许多天脉大陆武师梦寐以求的目标,就是当下的柳义也不例外。
但是武学之一道能达先天的,据说十万个练武者中也没有一个,比如:就柳义生活的这个叫明新州的,属五品级别建制的地方,其治下共九县,有二百多万人口,目前听说到的仅有五位先天武师。
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几位先天武师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那就是他们刚一达到先天,就不知为何,拼命地往外面跑,似乎是想去找什么东西,竟然没有一个是愿意呆在原地,只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个别的回来,然而竟然是发现他们颇为沮丧,一副如霜打的茄子闷闷不乐的样子。
不论何家何派武艺,均离不开刻苦砥砺和持之以恒,“五形拳”的炼法是“小成三年中,大成十年功”。柳义拳法小成已二年多,当年十四岁的他竟能突破三级巅峰达到四级初阶,也就是大陆上俗称的“中阶武师”层次,而今,已达五级“巅峰”,意谓着不久之后便可向六级冲刺。
“呼!呼!呼!……”。
只见,柳义在自家亩许大的院子内打起“五形拳”,时而形似游龙,时而动若虎豹,又或屈曲盘绕如蛇状,又或鹤立群鸡、稳若磐石。
“嗖!……嗖!……嗖!……”。
片刻之后,他的身躯竟然比之前快了几倍,如闪电般不停地移动穿插起来,窜奔跳跃,辗转腾挪,抑扬吞吐,拳脚如风。
整个套路打下来,那真是拳脚刚劲,力大千斤,吐纳绵长,气息浑厚。
内行人如在此时看到了,就知其已得其中精义。
打完了拳,微微喘几口气,他抓起一块挂于竹竿上的一厚厚蓝色布巾,擦拭干净身上的汗水,已是天色微明。
柳义想了想,看看还有些时间,就返回屋中,拿出来一杆丈余大长枪,接下来,就在院子里面练起了当今大津武术界很少有人能见识到的不传绝技——内家“游龙十三枪法”。
其实,这个枪法并非传自祖上,而是由他读书时的启蒙老师“孟夫子”所传授。
据称,内家枪法在大津国的传承并不多,使用者多为军中的大将,在世俗的战场上运用,那可真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封妻萌子的绝学。
听说“孟夫子”也是年轻时得自于一南郡的大儒,对柳义那可是又看面相、又进行试探,在整整考察了五年之后,于他十二岁时,才肯教给他的。
枪杆的木材是大津国北方所特有的白蜡树,柳义这边的南方地区没有生长。从外表看,枪身笔直如切,枪把粗如鸭蛋,枪头粗如鸭蛋黄,表面泛出青光,连一点疤节都没有,枪头不比枪把细多少。
整根枪杆沉重密实,又长又沉,常人两只手端平都难,很不好使,如发力一抖,杆身“呼呼”直颤,虽然振幅不算大、但持久。按“孟夫子”的说法,这根枪杆对于一般的武师来说都是比较难找的,就是他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搞得到。因为,这得要有专门的人员,按照实战要求,根据一定的选种、择地、种植、护理等秘法来培养出来的。
从白蜡树苗只有一米高时就开始修剪,只保留树顶几片叶子,不允许长任何侧枝,为的是限制其生长速度,并使树干笔直。
而且更为夸张的是,还要一天十二个时辰时时关照,为之浇上药水,不能让其长虫,否则一受虫害就留下疤了。
同时,它们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能种得太密,以至光照不好,树木就会弯曲,那就变废材了。
如此下来,一片符合要求的向阳之地,根据秘术种上一百根,二、三十年关心下来,能成十根就很不错。
只见柳义站在院中,双手抓住枪把,重重复复地做起了了三个基本动作——“拦、拿、扎”,这也是他每天晨练的必修课程,因为“游龙十三枪法”其他的种种玄妙动作和招式都可以从中演化。
柳义挥汗如雨,心无旁骛,待这三个基本动作足足重复了上千遍,他又在院中练起了“大枪桩”——
手臂向前伸开,右手抓住枪把,把丈长的杆子端平,身体如雕塑一般一动不动地站定。
不久,“哆!……哆!……哆!……”,柳义全身的关节、骨骼竟然微微抖动,奇妙地和白蜡杆大枪抖动的频率同步,人枪合一即枪和人浑然抖成一体,这一端整整又是半个多时辰,直到腰酸背痛,四肢麻木,他才停了下来。
“孟夫子”常常捋着胡子,满脸自豪地对他说:
要练过“大枪桩”,才能听懂自己的枪,枪和人才能互相感应,一摸枪杆习练者就知道枪想干什么,任何加在枪头上的一点小小的力量都能清晰地感觉到。这就是所谓的“听劲”!
据“孟夫子”说:他的师父,也就是那大儒,能一边骑着快速奔驰的骏马,一边飞快地舞动大枪,疾如闪电,瞬间刺出,点死石灰墙上的一只苍蝇,而更让人惊叹的是,那些石灰上面居然连一点点的痕迹都没有留下,可见其听劲之好,枪法之高。
而“孟夫子”他自己只须运用内劲,枪头一点,无论是一般民房青砖墙角的小砖或者是州城城墙墙角上的大砖,想卸下那块就卸下那块,决不含糊。
这靠的当然也是听劲,如果是使用身上蛮力的话,就是把枪杆子撞断了也是行不通的。
当然,柳义目前只练了二年多,虽然运用起“游龙十三枪法”自信可以克制住同阶中的甚至是比他功力高上一些的其它对手,但是和“孟夫子”等出神入化的高手境界比起来,还是有相当差距的,大概连砖角都卸不下。
举目四顾,远近村庄炊烟袅袅升起,邻近村户烧煮的饭菜,阵阵若有若无的香味,随着晨风从空气中飘来,更是激起了柳义进食的欲望。
习武之人本就比常人更容易耗能,何况柳义又是在长身体的非常时期!
洗漱,更衣,带上弓箭、朴刀、大枪,关门,几个动作一气呵成,沿着小路冲下山坡,一路小跑,向村子东头的“孟夫子”家里奔去。
刚入村,柳义眼尖,远远就看到村西的张大婶跟五、六位外村的中年农妇,头戴斗笠,身披蓑衣,肩上挑着箩筐谷箩,一路迤迤逶逶,说说笑笑地走出来。
顿时,他的心里不禁咯噔了一下:
原来,大津国虽有男子十八、女子十六方可婚娶的规定,但是,许多父母在自家孩子适婚年龄前两、三年,便托媒人找合适的人定婚。
眼前的这个张大婶有一个女儿,其芳龄已是十四,听村里面的人说,还是个长得如花似玉的大闺女,而且似乎她们家人就是看上了柳义,于上个月特地找人向柳敬说媒,但深知自己儿子性格的他以各种理由把它推掉了。
“大婶好早,去田地里割谷子啊。”
狭路相逢,柳义看看躲不过了,只能硬着头皮,连忙刹住身形,面带微笑,抱拳行礼,向张大婶招乎起来。
瞥了一下她们挑的箩筐和谷箩,发现中间放着镰刀、细绳之类的工具,心下知道,那几位农妇大概帮助大婶收割谷子的“换工”好友。
柳义清楚,秋收是世俗天脉农村的村民们最繁忙的收获季节,成熟的谷子是不等人的。
所谓“粒粒皆辛苦”,为了让谷子颗粒归仓,他们必须抢在阴雨天到来之前,将所有庄稼收割完毕,并尽快地把稻谷运回家。
为此,他们通常会采用“换工”这种简单而又有效的方式,也就是几个家庭联合起来,先集中忙活谷子成熟的这一家,然后另一家的也就差不多了,再接着忙活。
这样的互帮互助,既赢得了收割的宝贵时间,又增进了亲朋好友之间的感情,可谓一举两得。
“哎呀,柳秀才,这才几天不见,又长高几分啦。”
大婶摘下斗笠,露出一脸微黑健康的肤色,洁白的牙齿,嘻嘻哈哈地说:
“怎么,又想着上‘孟夫子’家吗?”
见他心急火燎,一步三急的样子,当下就猜中了几分。
“是啊,孟三立那黑大个昨天晚上到我这,临走拽了我好不容易存储起来的十两银子,说我这边从今天开始就用不着生火了,一日三餐都由他那解决,不过如此也好,今后‘孟夫子’家就是我的厨房啦,如此的待遇怕是州县的太爷也是无福消受吧,哈哈。”
说罢大笑起来,蓦地闪过身子,让开道、抱个拳,接着一窜一奔,边跑边回头道:
“好嘞!别耽搁大婶了,小子告辞。”
一溜烟,拐过一道弯路,瞬间不见了人影。
张大婶瞪眼望了望早已消逝了柳义身影的方向,似乎还有些不舍,回过头,一边赶路,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喃:
“哎,这秀才,溜得好快,早知如此,无论如何也把他叫住,去陪陪咱家老头子喝上两盅。”
“陪老头子是假,分明是看上了人家,想让你家小晨跟他套热呼吧?”
旁边的一位圆脸妇女瞅了瞅张大婶,大有深意地说。
“啐!别胡说。”
大婶笑着,拍了一下圆脸妇女,口是心非地说道:
“小晨今年才十四岁,离官府规定的谈婚论嫁的年龄还有两年,再说了,我们小晨也是亭亭玉立、水灵出众的姑娘,又知书达理什么的,有哪一点配不上他,是吧,王大妈?”
“啊,小晨倒是个不赖的闺女,可这秀才好生奇怪,又是携刀又是带枪的,衣着分明也是一副武者的行头。”
王大妈也是看了看,随后一脸疑惑,甚是不解,又说道:
“就说我们村的那个王秀才吧,人家那可是不一样啊,出入都是顶戴圆帽、脚踏方屐的儒服打扮,整天还唠叨着什么‘圆帽象天、方屐象地’,还说不停地说‘天圆地方、顶天立地、外圆内方……’什么的。”
“嗯,这就是此子与其它秀才的不同之处了,听我家老头子说,他七岁便习文炼武,十四岁武学已达四级,当年居然也中了秀才,今年满十六岁,就武功和文才来说,就是整个明新州的年轻一辈中也没有几个超过他的。”
说着,脸上露出几丝羡慕之色,又道:
“只是,此子性格沉稳,极象个成年人,同龄好友没几个,就本村的七、八十个年轻人,他唯独跟孟三立,喏,就是村上唯一的举人‘孟夫子’的小儿子交往,俩小子时常结伴上山,狩猎采药,有时在山上一连好几天都不回家,父母也不管,听说是叫做什么武者的‘历练’,不过为人心性倒不差,捕杀到大型猎物,还会分些许肉给众位村邻的。”
说到这,她不禁想起了十余天前,柳义送上门来的那一大块足有五、六斤重的野猪大腿上的腱子肉,吞了吞口水,接着又道:
“说到不拘于文人学士的装束,这小子平时做人处事也是淡定重容,对别人家的什么好话啊、坏话啊什么的也没放心上。据说,‘孟夫子’和秀才的父亲是生死之交,有一年‘夫子’得了急症,别的医师都是束手无策,还是柳医师从阎王爷的手里硬是把他的老命给拽了回来的,据说……”
边走边聊,涛涛不绝、不遗余力地继续讲解柳义的相关事迹。
此时,柳义刚到村东的“孟夫子”那一排宅户前院。
“……义哥,来了!”
一个熟悉的大嗓门蓦地窜入了柳义的耳根,直震得有些嗡嗡作响。
“……接俺一招!……嘿……哈!……”
又是几声急促的如同炸雷般的响动,一个身材魁伟、大汗淋漓的黑大个双手轮起正在操练的一个大石锁,“呜!……”地带起一阵狂风,甩手向柳义砸来……
说时迟,那时快,有着小箩筐般大小的青黑色的大石锁如黑虎扑食一般瞬间袭来,眼看柳义就要被它生生地砸成一坨肉饼。
蓦的,“啪……”的一声。
原来是柳义早已闪身退后一步,绷紧全身,弓身出左手,成“手挥琵琶”的架式,运劲于掌,拍打在石锁上。
“噗咚!……”
沉闷声响起,三百多斤的大石锁砸在左脚前方半尺处,刹时尘土飞扬!
“啪!……啪!……啪!……哈哈!好!好!……好一个举重若轻啊。”
一个身材高瘦,脸色稍许苍白,年近六旬的老者现身门前,哈哈大笑,击掌赞叹。
这位老者自然是孟贤“孟夫子”了。
孟贤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在文理村有田产一、二百亩,属小康之家,自幼聪颖,通熟儒学经典,博学多才,风水星相、占卜算命等等样样精通,武功修为亦很高,且二十五岁时便中举人,但极不喜官场的虚伪和黑暗,痴迷于追求武功极至。为此,他中举那一年便抛下其妻颜氏及刚五岁的大儿子孟齐,周游天下二十年,任侠好义,遍访名山大川,寻求天下武学,谁知多年竟然未能如愿,再怎么苦修,武功也突破不到先天,学无所成。
四十五岁时遂绝了这个不切实际的念头,安心回家继承祖业,出面让大儿子到县学任职,自己又开了个私塾,做起了教师育人的行当。
柳义向“孟夫子”行了个礼,谦逊地说道:
“‘夫子’过誉了,举重若轻还谈不上,只是刚才在面临危机之际,灵机一动,运用些许柔劲化解而已,倒是三立的神力又有所长进了。”
由于孟贤学识渊博,见多识广,为人豪爽,无丝毫酸气,又是启蒙启蒙老师,所以柳义对之十分敬重,而且还经常来讨教些学问以及借书什么的,又喜听其讲述当年见到的奇闻异事,以及各地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
“老爹,别听他的,俺别的不行,眼力没差,义哥方才那一手可是把试劲、运劲、化劲三劲合一,干净利落,俺学三年都学不来的……”,孟三立一边擦着汗,一边不停地嚷嚷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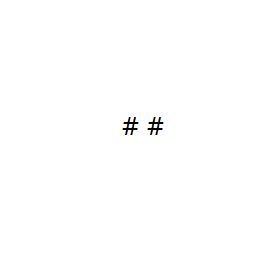
最新评论